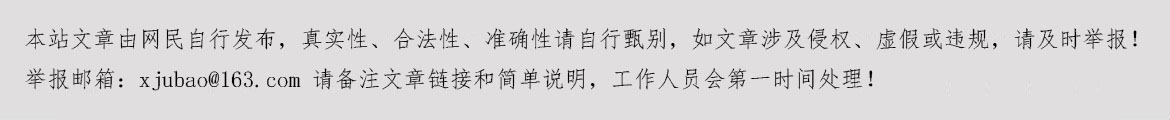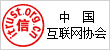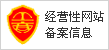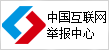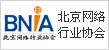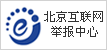“封控”结束,“逃难”开始
2022-10-03 17:11:00
5月16日,上海长达一个半月的封控,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放宽:
不再限制离沪,部分铁路逐渐恢复了正常。
街头依然萧索,绝大多数的店铺、企业,都没有开张;一些饭馆即使恢复了营业,也只能外卖,禁止堂食。
但是,有个罕见的例外之处:虹桥火车站。
解封第一天,就有超过6000人,乘火车从上海离开,到5月25日,随着增开更多列车,单日乘车离沪者增至3.5万人。
此外,还有通过自驾等方式离沪的。“独自骑单车上千里回老家”等新闻,比比皆是。
这种多年罕见的景象,是“瘟疫时代”种种魔幻的冰山一角,渗透着众多普通人的泪水。
然而,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,这种令人嗟叹的场面,已经发生过多次——其背后的种种社会因素,甚至比疫情本身,更发人深省。
当代美国学者弗兰克·M·斯诺登,出版了一本新书《流行病与社会》,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,非常值得一读。
千辛万苦,只求跑路
离开“半解封”的上海,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首先,要向目的地进行报备——光是这一关,就把不少人死死卡住。
一些幸运者,向目的地(通常是自己老家)的居委会或村委会进行报备,一番“求爷爷告奶奶”,终于得到了允许。
而这,仅仅只是购票离沪的最基本资格。
接下来,是一边收拾行李,一边“削尖脑袋”抢火车票。
为了一张票,不少人不得不求助于灰色渠道,加价几百元、上千元。
接下来,是在48小时的核酸有效时段内,设法赶往虹桥车站,坐上火车。
由于很多公交尚未开通,以及从家到车站之间,可能设有很多封控路障,对很多人而言,通往虹桥之路,堪比一场艰险的长征。
有人乘坐价格近千元的黑车,来到车站的一刻,对黑车主充满感激;
有人冒着酷暑,骑共享单车穿行几十公里,或者,拖着行李箱步行六七个小时;
还有人前一晚就来到了车站,打地铺过夜,却又担心身边的行李,整宿不敢合眼。
等候进站的长队,从车站大门口,一直排到高架桥上。
而此时,一些人的核酸有效时段,已经接近48小时的尾声。
直到进站乘车的前一刻,依然有人因48小时的核酸有效时段,仅仅超出了几分钟,而被拒之门外……
相比之下,知名歌手罗中旭,是非常幸运的。
老家在天津的他,在上海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封控后,终于抢到一张二等座车票,在5月23日登上列车,离沪回乡。
乘坐高铁时,他和其他众多乘客一样,穿着防护服,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,即使饥渴难耐,也不敢摘下面罩喝口水。
终于熬到终点,他晕晕乎乎、两腿发软地走出车站,外面是三十度的高温,但防护服依然不能脱下。
然后,他和其他众多离沪回乡者一起,被安置在一家酒店,开始了十四天隔离。
“进了酒店房门,脱下防护服,浑身都湿透了,就像从汗水里捞出来。全程十个钟头,没喝一滴水,暴汗虚脱,这就当减肥了!”
——这一切,难免让我们想到书中,欧洲黑死病期间的“大逃亡”。
很多住在伦敦、巴黎等大城市的中产之家,放弃了家业,逃到人烟稀少的乡村,或者山里。
路上遍地尸体,不少人为了避免与之接触,穿上特制的高底靴,即使三伏天也身穿严冬的衣服,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就这样长途跋涉至少一天一夜,才终于来到远离人烟之处,然后,将鞋子和衣服就地扔掉或者烧掉,找个小河,跳进去清洗一番……
而这个过程,也导致一些人感染风寒。
如果是一家几口人逃亡,感染风寒尤其是发烧者,通常会被其他家庭成员视为瘟疫感染者,被驱逐离开,任其自生自灭。
这类惨痛的历史场景,仿佛一直阴魂不散、不断轮回……
逃离在“黎明”
如今的众多离沪者,在疫情封控前夕,大都并不想离去,都期待着非常时期尽快过去,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
此后,他们经历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封控。
而他们的“逃离”,是在熬过至暗时刻的黎明时分,也就是即将全面解封、一切如常之时。
可想而知,其中的大多数,不是特殊时期的“逃难”,而是在这期间,已经想好了、铁了心:
“我已经对这个城市不抱希望了,只求一走了之;即使这里一切恢复如初,我再也不打算回来了!”
根据近期的一项调查,超过500万的外乡来沪务工者,都表示在封控期间,多次考虑过“要离开上海”。
他们当中的多数,都是上班族,封控期间,很多人的公司倒闭了,薪水突然断掉了,下个月的房租,和各种生活成本,都成为燃眉之急;
也有人是投资者,在上海开饭馆、办公司,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,如今血本无归。
然而,上述种种原因,也只是表面,更深层次的,是内心深处的长久创伤。
那个在大家长期以来的心目中,开放度国内顶尖,充满机遇和魅力的“魔都”,在漫长的封控期间,仿佛轰然坍塌。
依然高楼林立的上海,变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感、不安全感,无情无义,甚至即使有钱也可能陷入“饥荒”的伤心之地,一个随时可能将众多普通人活活吞噬掉的巨兽。
“从此逃离,再不回头”,是一种自发的避险,也是在封控中历经漫长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权衡,最终的理性选择。
如书中所言:
疫情下的城市,除了更高的人传人风险,还有缺粮、缺水、缺医少药等次生灾害,有些时候,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。
逃离城市,是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策略,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少数幸运者的“特权”。
呼唤大城市的人间温情
“平时灯红酒绿、浮华无比,一旦出现疫情等自然灾害,便沦为丛林——尤其是普通人,所有的个体,生死存亡和各种悲欢离合都变得无关紧要,随时可能被牺牲掉。”
“这是自古以来,疫情期间的都市常态。然而,一个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,不该再重复此类悲剧。”
书中在讲述了很多历史上的疫情灾难后,大声疾呼人间温情,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政管理,更需要转变观念,将“灾难之下,适者生存”的原始丛林思维,置换转变为以人为本、注重个体尊严。
尤其是,能够“逃离”的,哪怕绝对人数再说,在为数更加庞大的“外乡谋生人”群体中,也只是幸运的少数。
即使目前离开了上海,回到了老家,或许,在并不久远的将来,也会再找个和上海差不了太多的大城市。
在工业社会,绝大多数劳动者,都对大城市有着格外的依赖。
从上海,到其他各大城市,在封控结束后,其日常运行的各个环节,同样离不开来自五湖四海的众人。
如果没有吸引和留住“外来人”的魅力,其繁荣就会变成无根之木,难以持久。
这次“逃沪浪潮”,是对上海城市治理的一张黄牌,一个长鸣的警钟。
但愿,教训之后,能换来反思,换来治理观念的全面提升。
但愿,书中讲述的那些“疫情之下的社会悲剧”,不要继续“周期性的无限循环”,能够在上海,永久地画上休止符……
图片/均源自网络
因公众号平台推送规则更改
请在右下角点下“点赞”“在看”
第一时间阅读文章
好看的人都在看